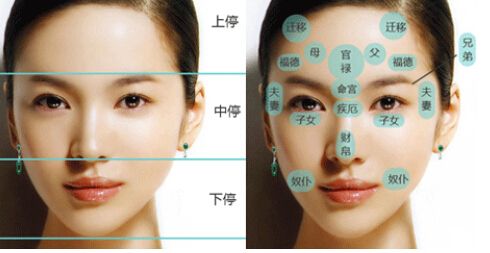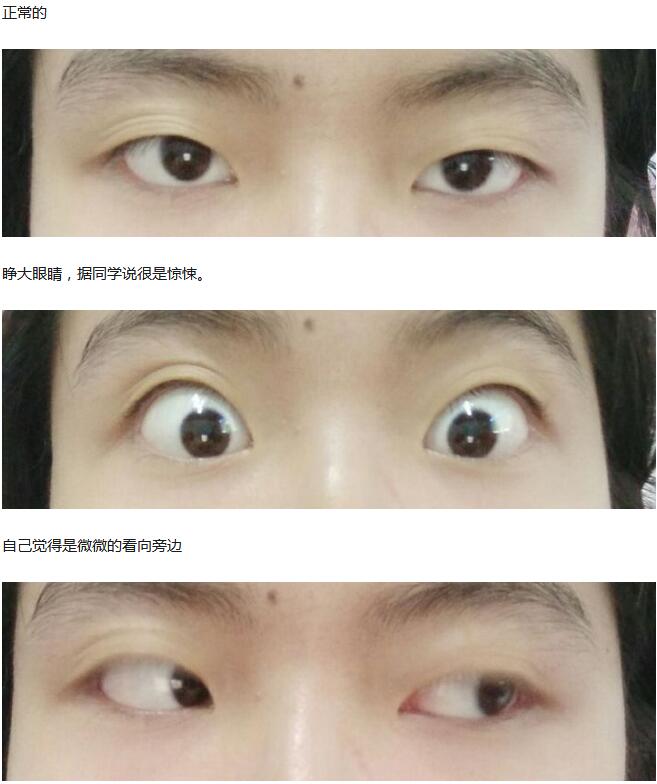两汉时期为相术的热潮,汉朝的建立,是出身农户的刘邦带领一帮来自各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的“猛士”在腥风血雨中撕打出来的。一个庄稼汉猛然间龙袍加身,一批出身游士、狗屠、吹鼓手、布贩、车夫、流氓、强盗的汉子,如陈平、焚哙、周勃、灌婴、娄敬、韩信、彭越之流,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

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对春秋战国以来已经失势的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天帝命论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充实官僚机构,汉高祖又征召天下贤士到京师分派官职,从军官吏也按功绩大小,规定各种待遇,这样,士人有了做官的盼头,士卒有了升迁的希望。西汉还设太学,从士人学子中培养官僚,士人学子从此有了从政并跻身上层的机会。汉武帝对招纳人才更为重视,以至于四处觅览,异人并出。东汉士人做官又有公府辟召、举孝廉等途径。但这些政治制度、仕进制度的改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的人事变动,总要造成许多人仕途际遇的不同,成功者的喜悦,落难者的颓丧和希冀,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感慨和思考,有的人不能从社会人事中寻找原因,只好以命的厚薄、气运的顺逆聊以自慰,或者为得官失职而思忖自己命运的吉凶。
这种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又为相术的发展和看相习俗的风行创造了合适的温床,从而酿成了中国自春秋以来的第一次相术热潮。秦汉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变化最为显著,这对相术的发展最为有利。仅刘邦一家,就有种种的看相记载,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一老人给刘邦妻儿看相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说法。如《汉书·高帝纪》说刘邦形相甚异,高鼻龙颡,美荔髯,左腿有七十二颗痣。又说他当亭长时,单父人吕公因避仇来到沛县令家,沛县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云拜贺,当时萧何主掌宴会,规定送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人坐于堂下,刘邦不揣一文,谎称送贺礼万钱,由于他平时常耍无赖,所有的客人都瞧不起他,但却被精于相术的吕公看破,认为他的相貌贵不可言,急忙出门恭迎,邀之上座,说“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并不顾妻子反对,将地位甚高的沛县令都求之不得的女儿吕雉许以为妻。
这样的相命之说,在汉代史籍中比比皆是,且一个比一个神异。但凡汉代发迹显达的人,如汉丞相周亚夫、长平侯卫青、宠臣邓通、吴王濞、淮南王英布、汉将军李广、丞相黄霸、御史大夫倪宪、美男子陈平等等都有这样一类相命的记载。
东汉,相术更加普遍,据《后汉书》记载,甚至连皇帝挑选后富贵人、美人、宫女、采女,都要派遣宫廷官员带着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官,择视可否,乃可登御”。至于皇后,往往都是事先相士言中的大贵人。如明德皇后,耒人宫时,太夫人让相士为她看相,相者相后惊叹地说:“我必为此女称臣。”章德窦皇后“数呼相士问息耗,见后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安思阎皇后13岁时,有个名叫芳通的相士见后,惊恐得拜贺再三,说她的相貌为“日角偃月”,为他从未见过的极贵的人。
这些命相之说,在此时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汉末建安十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江府小吏焦仲卿的母亲执意要休掉自己的儿媳妇刘氏,拆散这对恩爱夫妻,焦仲卿唯一能用来同残酷的封建礼教抗争的武器,竟是无奈的祈求“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可见此时相命风气的盛行和它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
看相的风俗已经是相当地淳厚,人们对相命的迷恋逐步到了狂热的地步。热衷于此的人们甚至进一步联想,把相命的内容还融合到与人相关的物件上,发明了由印玺看人命运的“相印法”,由手版、玉笏看人命相的“相笏法”、“相手版法”等,真是到了痴狂可笑的地步。
两汉相术热的显著标志
两汉相术热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相术理论的初建。如《汉书·艺文志》中就载有相人类24卷.又据《怀庆府志》记载,仅著名相士许负就著有相书《德器歌》、《五宫杂论》、《听声相形》诸种。可惜这些著作已经散逸,不复得见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术理论在西汉已得到了初步的整理。
如果说西汉的命学理论的初建,过多于形而下的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经王充的元气说哲学理论的概括,中国的相术才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并一下子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变种。
王充《论衡》是一部充满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论著。王充认为,构成世界的基础是“气”,又称“元气”,万物因此而生,由于“气性不均”而物体不同,天与地都是有形的实体,“含气之自然也”。天地无始无终,不生不死,没有生命和感觉。“天道自然无为”,不可能创造万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根本没有造物主。天不了解人的语言,不可能实行赏罚,“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人”。
这本是一种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陷入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他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个人贵贱贫富都是偶然的机遇,由无法解释的“命”所决定,而人的“命”,包括贵贱、贫富、贤愚,取决于受之自然,禀气而生的骨相。他在《论衡·骨相篇》指出:
“人日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
“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
“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正,睹富贵贫财,犹人见盘孟之器,知所设用也……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遇富贵之乐。”
这就是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命”,只要观察他的骨骼形体及皮肤纹路,就能作出灵验的判断。骨相既然是自然生就,禀气而成,它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结局,生就富贵骨相的人,不会遭受贫贱之苦;生就贫贱骨相的人,不会享受到富贵之乐。
东汉末年的王符也持这种“骨相”观,他所著《潜夫论·相列篇》指出:
“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
这里,“骨法”干脆就被喻为“禄相”的表征,可见“骨法”对于命相的重要。
王充的“元气说”和“骨相观”是对董仲舒“天命观”的有力抨击,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陷入了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泥坑,但从相术的意义来说,元气说和骨相观与当时的看相潮流甚为合辙,或者说是看相风俗的理论抽象。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相术逐步发展了自己的自然命定论。基于这种理论,后世的相书往往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人受气怀胎,皆禀五行。只日男,双日女,得其偏者形骨必俗,票其粹者神气必全。形有厚薄,故福有浅深,神有明暗,故识有智愚。虽吉凶贵贱纷论不齐,故神见于动作,形备于骨法,善恶有相,可得而知。”
相术由“奇形即圣人”到“形气”、“骨相”之说,再到明确地将“禀气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相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汉代盛行的特定的文化氛围使然,尤其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宇宙图式和董仲舒“大人相副”说的出现,都对相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充的“禀气说”的出现,相术开始自觉地整理自己的理论,看相习俗以更加快的速度弥漫于民间。可以说,两汉是相术产生质变飞跃的自觉时代。

相关文章